本篇文章4192字,读完约10分钟
陆铭
首先抛出我的核心观点,第一,不能简单地把最近经济增长下降理解为新常态。 如果万物都是常态,我们就没有改善的余地。 这会产生严重的误解。 第二,我们今天应该讨论经济政策,调整经济结构。 经济增长很快很好。 也不是不可能。

今天演讲的核心有土地、住房、工资三个词,其中非常核心的中间变量是劳动力流动。 首先,比较2000年和2000年中国国内移民空之间的分布,可以发现移民基本上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,中西部地区则比较集中在省会和大城市。 这一趋势到了年中有所加强,并未减弱。

如果把中国分成东、中、西来看,就会发现有一些变化。 通过计算东部、中部、西部移民的比重,可以看出2005年是拐点。 因为人口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,所以我们每五年只能看到一个值。 其实真正的拐点是在2003年。 ) 2005年,东部以移民的比重占绝对多数( 60多个),但之后有所减少。 从绝对数来看,移动到东部的人口较多,但移动到东部的份额下降了。 怎么会引起这种现象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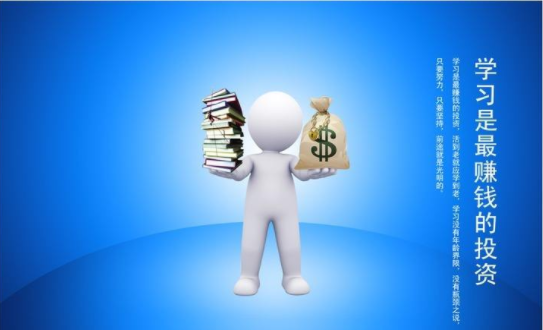
2003年,工资上涨速度开始加快,沿海地区还出现了农民工短缺问题,有些学者称之为路易斯拐点。 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,中国人口奖金的消失发生在去年,但2003年绝对没有到这种程度,当时中国还处于人口奖金期。 光从这个角度来看,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并不容易解释2003年的拐点。 2003年工资上涨拐点发生时,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于3,此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,到2009年开始下降,这也是路易斯拐点无法解释的。 如果路易斯拐点来了,农民的工资应该加速上升,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应该缩小。

另外,中国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,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。 中国工业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90%,但包括农民工在内,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仅为53%。 2003年的时候,城市化水平比现在低约10个百分点,所以在那个时期,中国出现了刘易斯拐点,他说需要特别注意。

房价提高工资
工资上升可以分为劳动生产率上升带来的两种类型,从这个立场来说,劳动生产率上升带来的工资上升是个好事件。 但是,另一个工资上涨是价格推动型因素造成的。 我不否认中国工资上涨的一部分可能来自生产率的提高,但我想更加强调价格上涨对工资的影响,也就是土地政策影响房价,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工资的增长。

2003年,土地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,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 1 .在总量上,更严格地控制建设用地指标,与维持18亿亩耕地红线有关。 在这样的目标下,中国建设用地指标的增长受到严格控制。 2、用土地供应的方法,实行招投标制度。 3 .从供给结构上看,用地面向中西部省份。 从大的角度来说,中西部是劳动力的流失地。 也就是说,政府希望通过土地供给方向的转变,向劳动力外流地供给越来越多的土地,限制劳动力流入地的土地供给,从而朝着当时人口流动的方向对冲。

2003年以后,中西部省份在全国土地供应中所占份额上升。 目前,土地供应的份额倾向于中西部,是人口流失地。 虽然人口流入地集中在沿海地带,但土地供给量相对减少。 基本的经济学知识表明,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导致人口流入地土地价格上涨,房价也会上涨。 我们住在上海,有这种感觉,2003年正好是上海房价明显上涨的拐点。

从中国各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与房价的相关性来看,根据拟合线2001年,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两条拟合线的斜率非常接近,2004年也非常接近,到2007年,东部城市拟合线的斜率明显向右旋转, 这意味着东部的房价比工资上涨得快。 但是中西部城市的房价相对于职工的平均工资几乎没有变化,这与我刚才提到的土地供应十分相关。

工资和房价的关联性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? 这有双向因果关系,另一方面,如果工资上涨,从诉求方的立场来看,会带来住房诉求的上升,从而带来房价的上涨。 反过来说,如果房价上涨,生活价格就会上升,如果生活价格上涨,劳动力去劳动力流入地的价格就会变高,去东部打工的人就会变少,这就说明了东部国内移民份额的下降。 对于选择去发达地区的人,只能支付他更高的工资。

工资上涨的理由是什么? 虽然这里区分了诉求和价格效应,但是如果工资上涨是由劳动生产力的拉动引起的话,劳动生产率本身就是经济竞争力,所以对宏观经济没有负面影响。 在价格方面,影响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地域分布,相对减少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供给。 这个地方的工资上涨特别快。 这样的话,工资和资金的价格关系就会发生变化,劳动力相对会高一些,稍微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面临价格上涨的更大冲击,要么用资本代替劳动,要么关门大吉,要么远离中国,转战其他快速发展中国家。

这被我称为过度的资本深化和过快的产业升级。 中国早晚有可能进行产业升级和资本深化,当你通过政策提高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时候,这个过程太快了,会影响经济的增长率。
我们最近的研究通过数据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最先回答了两个问题。 第一,能否看到房价影响工资的机制,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。 第二,这样的机制在中国的地区之间有差异吗? 确实有。 房价上涨和生活价格上涨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,最终传递到工资上。 这种情况在中国东部最常发生,同时这种机制也只在2003年以后存在。

中国东部的工资上涨得更快,除了土地和房价的因素以外,还有其他影响的因素吗?
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是,中国东部的人均gdp (或劳动生产率)是不是上升得更快了? 看看东部相对于西部第二三次产业人均平均产量的相对数量,计算出东部的人均平均产量除以中西部的人均平均产量。 如你所见,2003年以后,中国东部的人均产量相对较低。 那绝对是更高的,不能从人均gdp的角度解释我刚才说的工资上涨问题。

从另一个因素来看,中国从2003年开始实施严格的最低工资法。 我们收集并比较了各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,发现中国东部的最低工资不仅没有更快地上涨,反而相对缓慢地上涨。 这个东部工资上涨得更快,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,不是最低工资的推动,而是土地政策传导到房价,进一步影响工资的机制。

歪曲的土地政策
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
现在,通过给中西部更多的用地指标,农民工似乎可以在家门口工作了。 但是,从经济学的逻辑立场来说,如果试图用政策介入资源配置的方向,其结果必然是效率下降。 如果计算1998年到200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( tfp ),就会发现2003年发生了拐点,之后tfp的增长速度变慢了。

我们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各公司的投资、劳动力等要素,不包括基础设施投资。 然后,计算出这数百万公司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。 2003年以后,tfp的增长开始减缓。 通常,tfp的增长率大多是顺周期的。 也就是说,经济增长速度快时,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提高了,但由于这个tfp的增长率加速,资本投入可能不会很快。 正好在2003年以后,中国经济增长率较快的时候,tfp的增长速度变慢了。 这里发生了问题。

图1表示公司和公司之间的tfp的差异。 在市场经济中,市场力量必然会诱惑资源从低效的公司配置到高效的公司,如果市场运营,公司与公司之间的效率差就会缩小。 蓝线是表示公司和公司效率差的指标,到2003年公司和公司的效率差缩小,证明了市场正在配置资源。 2003年以后,这条线往上走了。 仅从样本中的公司(在位公司)来看,它们之间的tfp差距在2003年以后扩大,这一拐点更为明显。

图2显示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。 我们把公司分成东部公司、中部公司和西部公司。 东部线位于最低的位置,证明东部公司和公司之间的效率差距最小,市场力量最强,其次是中部,其次是西部。
在2003年之前,这三条线基本上是平行下行的。 也就是说,在东部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,但大家都在改善。 2003年以后,这条线开始分化,其中东部没有特别大的变化。 可以看出问题出在中部和西部,tfp的差距明显扩大。
这样的土地政策会影响东部劳动力的流入和工资价格,对东部不利。 是说对中西部有好处吗? 答案是中西部也没有好处。
上述中西部的效率也在恶化,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效率,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无法维持。 这些事件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债务的大量累积。 让我们看看债务除以gdp的比率。 如果投入有生产力,那么投资下去,gdp也会上升,债务-gdp比率不会上升。 这个比率的上升意味着进行投资后,产量没有同步增加,一般被认为是危险的事件。 图3的横轴表示各省的人均gdp,纵轴表示该省的负债率。 如果画拟合线,这条线整体向右下方倾斜。 从图中可以看出,整体收入低的省份负债率高。 红色圆圈部分是整体负债率超过40%的省,除海南外是中西部的省。 行政通过参与资源配置的地区快速发展政策,表面上看似在支援欠发达地区,但实际上危害了中国东部的竞争力,另外由于投入产出效率低,也给中西部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。

中国必须强调结构红利
最后一面将今天讲的事件总结成几句话,一面进行扩张的启发性思考。
首先,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理解为新常态。 很多人强调中国的人口奖金已经结束,外需也没有2008年之前的增长那么快。 其实,最近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,已经是从2003年开始,我们在高增长的时候埋下了低增长的祸根,问题出在了一点干预的政策上。

第二,如果我今天说的是正确的话,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来说,必须强调结构红利。 该奖金特别强调城乡间和区域间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。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,中国劳动力问题总量过剩,局部不足。 如果这八个字是对的,就不是路易斯拐点。 总量过剩,局部不足,必然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。 否则,把过剩的地方的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力不足的地方就行了。 局部不足一定是劳动力转移障碍的问题,而不是人口本身路易斯拐点的问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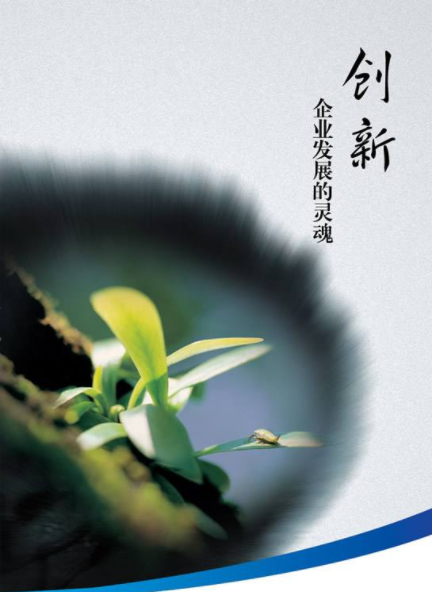
如果我今天讲的是对的,新常态成立了,我想只有一种新常态,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,但是政府只能发挥得更好。 在资源配置方面,人的出行方向和用地指标的配置方向必须一致。 政府应该做的不是与市场作对,而是顺应市场经济规律,弥补市场的失败。

(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、复旦大学教授。 本文整理编制了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安泰·在政论坛的演讲,经作者审查预约。 郑景昕,业务邮箱:郑景昕@ thepaper )
来源:企业信息港
标题:“中国土地政策怎么影响了经济竞争力”
地址:http://www.quanhenglawyer.com/qyzx/4559.html
